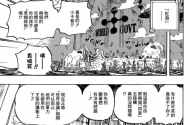晴窗绿影读董桥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读董桥,在这睛窗之下,轻抚午后淡淡的秋阳,衬着满目婆娑的绿影。 董桥长于台湾,跋涉南洋,访学欧陆,落户香港,沐浴欧风美雨,英语已入化境,怎么说都该是个洋派文人,但他笔底潺湲的又无疑是中华文化的涓涓细流,旧日襟怀就是放在大陆也少见,而且旧得倔强,旧得有诗意。他坐在港九之间的高楼里,心中乃是温存不去的明山秀水,摩挲旧版书籍、旧墨旧砚、竹刻玉雕、书画文玩,阅尽中西文化的春风秋雨,静看历代往事的苍凉寂寞,经史掌故随手拈来。一张藏书票,一本皮面旧书,一座绿意斑驳的铜炉,相晤之间已积了长长的香缘。我相信他娓娓叙来时,眼里必定满是朦胧的泪影,毕竟在幽谷中亮起这一窗灯火,靠的不是迂夫子的自怜自赏,而是对历史余温的动情抚摸。 旧派人做旧派事没什么不对,鼠标扫得出大知识毕竟扫不出小情趣。炉边灯下喝茶,一页一页翻读纸本书,追念旧时人事旧时悲欢,在我们来看,本来就是不可多得的欢愉;到了董桥那里,更是“不致辜负了那一抹旧时月色”的幽趣。董桥有很多文章写他在欧洲猎书的轶事,巴黎、伦敦、威尼斯等地的百年老书坊在昏暗中渗出丝丝沧桑的妩媚,就连陈年樟脑味都呼应着读书人末世的浪漫和偏执的癖好,纵然远隔千山万水,那种指尖与纸页相触的瞬间享受没法不让同样爱书的人会心莞尔。 民国是董桥这样怀旧情深的人心中一张永远昏黄的老照片。诡异而暧昧的民国,在他看来潮落之后还遗留几分风流蕴藉,悲欢褪去便是一幅绵长的手卷,只是静静地写实,便让人静静相对。梁实秋、台静农、胡适、张大千、凌叔华等民国大师从历史后院走出来,一个眼神一个转身,传递的都是师长如友、薪火连绵的温润情怀。写梁实秋,他淡淡一句:“我从十几岁就读梁实秋读到我老了。”浅浅的话里竟能嚼出连篇滋味。台静农的一句“人生实难”教人窥见的不只是他满鬓的银霜,更有八十几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胡适,还是那么聪明而世故,在掌声和私语之际,仍然儒雅地留下一点幽默、一脸微笑。若说兴叹,那是目送最后一批文化贵族远去的欷歔;若说痴恋,却早已不是深宵梦醒灯火萧疏的怅然,而是缠绵心中的对柳梢月色南窗梅影的供养。 读书人本来就载不动过多歌哭的沉郁,情到深处只需纤细的笔下个脚注,往事就已清风明月了;只是政治的几番风雨依然不能消停深深庭院里的花开花落,推开紧掩的那扇窗,寻到的还是那缕旧时花香。董桥写道,中国大陆倒是有几位女演员发髻一挽就很有民国味。他最欣赏已患病逝去的李媛媛,“从她矜持的颦笑中找到的却是宋家姐妹气韵里那阵久违的民国味。”那一身民国闺秀气质说穿了就是浓浓世情里的淡淡清水,这使我蓦然记起李媛媛在《围城》里的表演的确不是一般的婉约。 如果不问董桥的年龄,很难把那些清新灵动的文字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联系起来说道。董桥为文老却没有皱纹,一字一词都经过拈量,文章江山如磐,清澈似水,写出了宋词元曲那般临风的玉树。他认为,白话文要有文言文的凝练,文字需琢字而成,不论方圆都不露镌琢之痕,却显见镌琢之妙;最后若能浮出那么一丝古艳,想必更妙!董桥玩文几十年,深谙留白之道,笔法脱俗如新,尽管年逾古稀,却不见芳草迟暮,心中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片苍翠田园的倒影,那一帘春灯秋月的朦胧,还有瓜棚豆架下笑看岁月烟云的淡然。 修词炼句很容易使文章陷入效颦矫情,如果没有故事命脉的支撑,拧一把流下的都是浓艳的脂水。董桥文章之“老”就在于说故事。“阅世一深,更处处是‘事’,顺手一拈,尽得风流。”他有满肚子讲不完的故事,深写浅写,虚实相托:书里书外的事、师长文友的事、从前的事、这一代的事……在浓墨淡痕中滋养文人清雅的癖好,追寻早岁的沉香,重拾飘零的客思,间或夹杂家国的牵挂、归人蛩然的足音。“我”字摆了进去,牵扯起萦怀挂心的俗情冷暖和直面时世的长枪短炮,满纸都是英式隽永明人遗意。涉世一深感悟的年月,那是不一样的哀矜之后的苏醒。 港台和大陆文坛确是两番不很一样的风景。相比大陆作家二十世纪下半叶遭遇的集体性大震荡、大分裂、大痛苦,港台作家或许少了些许苍凉旅程中哭之笑之的历史悲情。但那一页痛史注满的却是千古抹不掉的羞,如果真要这样才能催生出风雨中凄美的花朵,人间还是少些这类祸殃为好。没有大跌宕,并不意味没有大情怀。几十年的光阴际会是一份隐隐然的眷注,董桥字里行间始终素静,忽忽闪动着文化那点幽明的烛火和读书人那份良知的传承,偶然漏下几声书生的呼号,也分明潜藏着政治的横披、民生的斗方、入世的赤诚,绽放的绝不仅仅是刹那的美丽,更有磨刀有记的乾坤正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多少读书人的操守化为流水的呜咽,而繁华声中游祟的淡泊又不过是薄薄一层窗纸。抛开浮媚中的骚动已然是莫大的挑战,揭示安分人生里“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更是最沉潜的体悟,董桥做到了这两点,比起风雨过后的凄惶与忏悔,他下笔更坚实——“隐隐作痛的感觉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