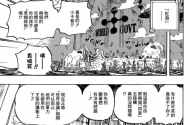要不是张艺谋,我真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牛的一部电影名叫《人生》
上一次吴天明进入公众视野成为讨论的焦点,还是2016年因为遗作《百鸟朝凤》在排片降到不足1%时,制片人方励直播下跪,从而掀起了一阵观影大潮。
吴天明,这个名字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听说过。 实际上,在新时期中国电影史上,吴天明曾经是一个神话。 在大陆,吴天明代表着一种“魅力”;在香港,吴天明象征着一种“奇迹”;台湾电影人则因为“大陆有吴天明,台湾没有”而感慨。
“当时台湾电影界犹如一盘散沙,缺乏有实力、有远见的制片统领人才,吴天明的形象正好补上这一空缺”。 从 1983 年到1989年担任厂长的六年时间里,他让全国发行拷贝量倒数第一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一跃成为正数第一,一度被称为中国电影的圣地。 可以说,在80年代,西影厂的影片基本上代表了中国电影的水平,以至全国都发出了“西望长安”的惊叹。
同时,他大胆启用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何平、周晓文、黄建新等有艺术创新能力的年轻人,培养起了他们这一批日后被称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年轻人,吴天明也因此被尊称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教父”,被张艺谋、陈凯歌等一代导演视为父亲般尊敬。
从导演身份来讲,吴天明导演的电影并不多,在75年的人生中,只有区区八部:《亲缘》、《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变脸》、《非常爱情》、《首席执行官》、《百鸟朝凤》。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他于1984年拍摄的《人生》。
01 马云曾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路遥,“18岁时我再度高考失利,应聘了五六个工作都没人要,只能去当送杂志的零工,是《人生》改变了我,让我意识到不放弃总有机会,否则我现在还在踩三轮车呢。” 虽然不知道“马爸爸”到底是怎么从《人生》中看出“不放弃总有机会”这个道理的,但路遥的这部作品在被吴天明改编成电影后,的确成为了1984年中国热议的话题之一。
从影以来,吴天明一直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探寻真实之路”。 在经过《亲缘》和《没有航标的河流》两部电影的“漂泊”之后,他终于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所追寻的东西,就在他生命的起点——即生他养他的陕西农村。
这部电影可以被看作是吴天明风格的成型之作。 《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一个十足的“渣男”。 高考失利后的他,在村里当了一名小学老师,虽然不能算是光耀门楣,但是跟挥了一辈子锄头的父母相比,已经能算是熬出头了。 然而影片的第一个场景,是高加林和父母三人在点着煤油灯的土屋子里愁容满面—— 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高中毕业,把农民的儿子高加林从小学教师的位置上挤了下来。
所以没办法,他只能“弃文从武”,挥起了锄头当起了农民。
这时,“村里一枝花”巧珍,这个被吴天明塑造成“完人”的美丽女子,主动对高加林表达了爱意。
眼看着两人顺理成章就要结婚了,高加林又凭借当局长的叔叔得到了一个到城里当记者的机会。 一心想着能“跃龙门”的他,到城里之后又被干部子弟亚萍追求,因此变了心,抛弃了巧珍。 亚萍对于高加林来说,代表的不是爱情,而是“城市”,是挣脱土地束缚的机会。
表面上看,这又是一出“深情女子负心郎”的故事,但实际上,《人生》正如片名所预示的那样,讲述的是“人生”。 电影里,好像所有人都在“待价而沽”。
巧珍主动追求加林,发生在他成为农民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巧珍觉得自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村妇,配不上小学老师高加林。 只有他也成了农民,两人的地位才平等。
一开始,巧珍的父亲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喊着要打断加林的腿。但在加林到了城里当记者之后,又默许了女儿的选择。
而加林的“高升”,则是因为他叔叔被从新疆调来当局长了。 加林抛弃巧珍时,巧珍的不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两人的关系又一次变得悬殊起来,她再一次“配不上”他。 而加林和城里女子亚萍的“爱情”,在他被举报走后门后,自然而然地就破灭了,亚萍只是象征性地小小地挣扎了一下,就接受了这个现实。 高加林甚至连挣扎都没有。
在《人生》里,在那片黄土地上,从未有过“公道”二字。仿佛在告诉我们:人生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人生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直到今天,这种深入骨髓的“处世哲学”还在时时刻刻发挥着作用:官富后代的特权、门当户对的婚姻、走后门...... 02有人说,路遥的《人生》参考了司汤达的作品,高加林就是中国的于连。
但吴天明说:“高加林既不是保尔·科察金,也不是于连·索黑尔,而是一个彷徨于人生十字路口,还没有找到正确方向和坚定信念的青年典型。” 王富仁教授也说:“在高加林这一人物身上‘聚集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各种复杂矛盾’。他是处于新旧交替期的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富有历史深度的典型形象。” 而在皮哥看来,高加林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标本”式人物。
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高考落榜生,一个业余时间在报刊上发表诗歌的文学青年,一个无比向往城市生活的年轻人。 他在城与乡、新与旧、理想与现实之间被狠狠打击着、摩擦着、塑造着。 值得注意的是,高加林的两次恋爱都是被动的。无论是巧珍还是亚萍,都处在一个异常主动的地位。
巧珍代表的乡村,与亚萍所代表的城市,这两者都向加林伸出了橄榄枝。但同时,她们也都没有能顺利保全加林的自我。 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之中,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高加林位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
和巧珍在一起,意味着他要和一个不识字的女人过一生,意味着他将像祖辈们一样被土地束缚;
和亚萍在一起,意味着他失去了爱情,成为一个背叛者,一个不忠不义的人。 这样看来,无论是路遥还是吴天明,都无意塑造一个“陈世美”或者是“于连”。 高加林只能是高加林,他身上所携带的矛盾性正是中国社会的矛盾性。
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并没有给小城青年以喘息,或者说是充分审视自我的时间。 生长农村的他们,怀揣着对城市、对现代化的向往来到城市,却依旧为城市所不容、所排斥。 在城市/乡村这对交错的镜像中,他们一方面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另一方面又无法洗净身上的泥土味,因此只能拥有尴尬的、暧昧不清的身份认同。
就像高加林一样,今天依旧有大量的小镇青年们被裹挟在横流的物欲中失去方向,迷失了自我。 这一定程度上算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无法忽视又仿佛被刻意忽视的巨大矛盾。
吴天明能从《人生》中挖掘到这一点,值得称赞。但是在《人生》中,吴天明也有败笔。 巧珍的形象塑造得过于美好。 这衬托得男主高加林愈发不忠不义,也使得“乡村与城市”这对矛盾用笔不均,明显偏爱于乡村。
亚萍的形象又有点单薄。 这一人物,和吴天明之后《老井》中的巧英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式女性”,也都是超出吴天明认知经验之外的人物。 因此,他在把握这两个人物时,遭遇了同样的失败。
03 在《人生》中,吴天明不仅开始直面人生,直面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并且有意识地将人生与黄土地联系在一起,将人生与自然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艺术整体。
因此有评价说:“《人生》第一次把西北黄土高原那大自然的雄浑之美和西北人民的善良质朴、博大之美融为一体,是西影的第一部‘西部片’。”
相信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那一幅幅大远景、全景镜头、空镜头中,感受到导演对这片土地深沉的无以复加的热爱。
当同时期的其他导演,还在沉溺于花哨的新技术之中时,吴天明第一次静下心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实之路”。 而这条路在接下来的《老井》中,被推向了更深、更宏大的层面。
可惜的是,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一向爽直的吴天明滞留美国整整五年。等到他五年后再回到中国,电影界又换了气象。 虽然吴天明始终认为自己初心未变,但那股子“真实”在后几部作品里,明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未能高超《人生》和《老井》。
或许,吴天明的经历,也从另一种角度印证了《人生》中的二难处境。 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城市/乡村的对立,而是政治与艺术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