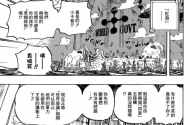梁振华:《冰与火的青春》真正起步于编剧的一次“累觉不爱”
编者按: 梁振华是在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经院文化之间游走无碍的通才,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打通文艺评论与创作的任督二脉,左手写论文专著,右手写影视剧本,凭论文专著年纪轻轻便评为北师大教授,同时编剧作品屡登央视、湖南卫视黄金档,收视表现出众。曾经还为多部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政论专题片担任撰稿,获奖无数,对主流正统思想、国计民生方方面面亦有全局立体的把握。做了多年编剧,如今又升级为制片人,由他历时四年打造的《冰与火的青春》正在湖南卫视热播,收视率稳定在1.5左右,稳居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收视第一名。近日独舌记者采访了梁振华先生,听他畅谈心路历程和宝贵经验。
(1)情怀溶于创作就像盐溶进水里 独舌:最近《冰与火的青春》正在热播,您既是编剧,又是制片人,先谈谈这部剧的创作初衷? 梁振华:这部剧原先叫《青春你好》,后来改名《冰与火的青春》,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因为“冰与火”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我对青春的某种认知或者说态度。炽烈如火、酷寒如冰,两种色调交织成一段百感交集的人生旅途。故事主人公一个叫江焱、一个叫夏冰,名字也扣在了“冰与火”这个精神内核上。我1995年进到大学,到现在整整二十年,先当学生,再当老师,来来往往见证了无数人的青春故事。早在读大学时就想写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当时想写长篇小说,后来有机会从事影视创作,就一直有强烈的冲动写一部作品,来传递我对青春的理解和感悟。
独舌:所以这部剧是融合了70后、80后和90后的青春体验? 梁振华:我觉得这几代人的青春共性大于差异性。不同的是关注的话题、情感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现在年轻人的思维更迅捷,更网络化、碎片化,接受到的信息量更大,不易屈从和妥协,也不容易相信,相比此前更有决断和主见。但无论70后还是80、90后,成长过程中所要经历的考验、创痛和成长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爱与痛、希望和迷茫,大体是一致的。所以,这部剧笔下的年轻人并没有非常明确的代际符号,我希望年轻人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独舌: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是代表了几种类型的年轻人吗? 梁振华:对,江焱、夏冰、肖一飞、林晓珑、苏克,每个人都对应了一种人格构成和生活道路。比如,江焱是一夜跌入冰窟的“富二代”,原本拥有一切,朝夕之间失去所有,再从零起步,再奋斗,这比白手起家更艰难。重心不是“富二代”,而是跌落之后的振作和攀爬,他的故事兼容了现实和传奇的色彩,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共鸣,觉得很励志,呼应了很多年轻人当下的成长处境。夏冰是一株勤奋的野草,自强自立,不求告,不奢望,只求靠自己的双手过上踏踏实实的人生。她的青春异常坎坷,但却散发着无处不在的温暖。肖一飞原先是游手好闲族,贫嘴,油滑,没什么理想抱负,他的理想就是爱情,他的青春依附于女朋友林晓珑而存在。可在爱情受挫之后,他痛定思痛,咬着牙关找回了自己的尊严。林晓珑表面上是比较物质虚荣的女孩(事实上她有家庭的现实原因),这在今天很常见,她的爱情选择一定会带来争议,但放在今天的环境下是残酷却又真实的。最终,她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苏克,好像特别受观众的喜欢,他老实忠厚,笃信善良与诚信的准则,虽然现实条件困苦,但始终不忘初心和梦想。也许苏克算这个时代朴素的理想主义样板,并不那么伟大高贵,但令人心生尊敬。这些年轻人,不同出身、不同经历,也有不一样的人格和理想,自然有不一样的成长启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角色都是我的朋友,我坚信,他们一直鲜活着,绽放着,在我们的身边,而不仅仅在故事中。他们构成了青春的斑斓图景。
独舌:罗浩那条家族恩怨的线,有点TVB的味道。 梁振华:设置罗浩那条复仇的线索,是为了让戏更有张力,让情节始终处于戏剧压力之下,而不显得零散。这条线一直暗藏潜伏着,就有悬念,观众会期待江焱和罗浩的最终PK。他们之间会在商场上进行博弈、进行智力和人格的对决。家族恩怨是一个叙事母题,这方面确实受到了TVB剧的一些影响,我从小就很喜欢看TVB剧,《义不容情》、《大时代》、《创世纪》……对人性和欲望的刻画都很鲜明,给我印象很深刻。这条阴谋线和青春成长的主体故事双线并行,江焱和小伙伴们的成长其实跟商战没有太多纠葛,我相当于在青春励志与商战恩怨之间做了一个缝合,也算类型的搭配和调和吧。 独舌:电视剧需要通俗性,需要考虑市场;创作者往往有个人情怀,尤其是您这样学院背景的人,如何在情怀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 梁振华:情怀溶于创作就像盐溶进水里,而不是挂在口头,停留在说教上。我固执地以为,从事创作,有没有情怀是有区别的。有些作品,纯粹就是为了逗人一乐,但我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和创作观念执拗地强迫我,总想在故事里装一些东西。任何题材类型都可以表达情怀——只要你想跟这个社会对话,只要你有对人、对现实和存在的态度,想完成一些价值和理念的传达。情怀这个语词,包容性其实非常大,随物赋形,有时候写大地可能是为了星空,写生活是为了揭示存在。像我写《我的博士老公》,轻喜剧的外衣下,其实有非常多的现实批判色彩,对于高校生态,对于权学交易和学术腐败,但所有的批判都指向我对大学理想生态的憧憬;再比如《冰与火的青春》,有人认为是偶像剧,但事实上它的叙事模式是反偶像的,写的是繁华落尽后青春的孤独和承担。情怀跟市场并不是一组矛盾,可以尝试对接和缝合,二者的纽结点,说得简单些就是一个好的故事,有让人玩味的人物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情怀就不是累赘,而是轻松后的冥想,浮光后的远方。这也许就是你说的平衡吧。
独舌:播出平台、评论界和广大观众对《冰与火的青春》评价反馈如何? 梁振华:播出平台湖南卫视看到这部阳光正能量的作品很喜欢,在播出档期、宣传推广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个戏开播后全国网和城市网收视率一直稳居全国第一,微博口碑指数也是第一,挑剔的专家学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对我们整个团队付出的艰辛努力来说是最好的回报。在我个人而言,收视数据背后,每天晚上有几千万观众,跟随剧情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经历坎坷,一起收获成长,这是一种巨大的“蛊惑”和吸引。这些天,在地铁里、小卖部还有机场,我都听见人们在谈论江焱的苦逼青春,谈论冰与火的爱情,我心里特别温暖,会觉得自己的思考和感悟,通过电视媒介的广泛传播产生了精神和情感方面的价值。这也是我在大学任教的同时孜孜不倦从事影视创作最大的精神动力。 (2)触电15年,学术和创作的相生相克 独舌:您是很希望介入现实、影响大众的学者,而不仅仅满足于在象牙塔里做学问? 梁振华:我对学院有两重态度,一方面我非常尊重学院,学院是人类知识文化谱系性传承的圣地。无论在什么时代,纯正的学统都不会丢失,都有甘坐板凳十年冷、甘于寂寞的学者在坚守,他们是文化的脊梁。我所在的北师大,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学者,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另一方面,我觉得学院应该要开一扇窗,把经院的文化和大众的趣味对接起来,实现双向互动,让经院文化有时代的生气,也让大众文化不至于过于轻飘,这样时代的文化空气才可能激荡流动起来,才是源头活水。同样,学者也有不同的姿态,并不是说所有的学者都要闭门在书斋里做学问,有些学者的舞台是书桌和讲台,有些希望把自己的所学、所思、所感面向社会进行更广泛的传播。我显然属于后者,很感激我所在的大学容许我这样的学者存在。 独舌: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只是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成为一种塑造时代的力量。 梁振华:与其坐而怨,不如起而行。哪怕只是局部地改变了一些人的思考和言行,也是很欣慰的事。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跟很多的制约性力量去抗衡、博弈,需要在夹缝中求生。尤其是做了制片人之后,才明白这个行业的艰辛与不易。 独舌:理论上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但有时候读太多理论也可能构成某种桎梏。对您来说,学术思维对创作是有帮助还是有干扰? 梁振华:习惯了抽象思维之后,再去进行创作确实常常有障碍,他碰到一切问题都习惯于理性的归纳和总结,但艺术创作恰恰是感性的,是形象先行而不是理念先行。作为学者和作为创作者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但我觉得还是有互通之处。我不倾向于把理论作为指导创作的准则,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方法论上去把握,面对一件事,一个问题,先去抓它的核心实质,尝试整体性地把握它,可以用比较专深、比较系统的方式分析它。学术训练可能会带来这方面的经验。如果创作者既具备了这种严谨思维,又不失天马行空的形象创造力,一加一就会大于二。我正尝试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独舌: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创作的? 梁振华:我2000年硕士一年级的时候开始“触电”,做了将近十年的电视撰稿人,大型文献片、纪录片、专题片做了不少,给《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三峡》《走向和谐》等很多央视播出的大型主流文献纪录片做总撰稿或执行总撰稿,纪录片领域的各大奖项基本上拿全了。熟悉我的朋友都说,很难把我当时做撰稿时那种特别工整、严谨、端正的文风,跟今天的《冰与火的青春》这样的都市青春题材叙事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我主动尝试的一种写作风格或方式的转型。毕竟,影视剧的写作与创作空间相对更大,可以给我更从容的表达自由,能够通过虚拟的叙事跟观众进行最直接的情感沟通。但是,很多创作领域的经验实际上是相通的。长年的影视纪录片创作让我收获了许多影像叙事的教训和心得,尤其在结构意识方面,还有对生活本相的观察和提炼。
独舌:您在大学读中文系,跟文字亲近是比较自然的吧? 梁振华:从小学美术和书法,在中学是艺术特长生,保送到大学进了中文系,发现在中文系里美术书法没什么用武之地,同学们都写诗写小说。而我一个铅字都没有发表过,特别自卑。我记得班上有个漂亮女孩,在牛仔裤上故意挖个破洞,旁边还用钢笔写了一行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说你太牛了(笑),然后她得意地拿出一首自己写的诗给我看,确实写得很好,我当时根本读不懂。当时我们那个班叫国家中文基地,都是一群才子才女,同学都喜欢写东西,而我基本没怎么动过笔,觉得很惭愧,要赶紧追上,就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定要勤写。大学前两年,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写,写了很多抽屉文学,一个字没发表,稿纸摞起来有一米五高。 独舌:都是什么文体,哪种风格? 梁振华:基本是散文、随笔和评论,也有小说,然后向报纸和杂志投稿,慢慢开始发表。从大三到大四那一年突然找到了感觉,一年内发表了一百几十篇文章,一个人发表的文章数量几乎是全年级的总和。那时也很奇妙,就是写着写着,突然发现遣词造句、布局谋篇变得越来越轻松自如,仿佛突破了自我表达的临界点。只要我想说,就能找到形式说出来。我真正的写作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独舌:青春时代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梁振华:余华。喜欢他在不动声色中所包藏的对生活的态度。文字异常冷静,但内里有汹涌的热情。我父母也都是医生,余华有一篇《虚伪的作品》, 讲他的生活经历,当时我看了就发现他讲的那些事跟我童年经历的现实非常相似。他的作品特别能通到我心里。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刻意模仿过余华的文风——“让阴沉的天空来展示阳光”。余华老师常来北师大,现在每次和他交流,当年阅读他的作品时那种揪心而又通爽的感觉常常浮现出来。 独舌:为什么没有走纯文学写小说的道路? 梁振华:从文字到影像的转轨,是这个时代的文化转型趋势,这一点已经不需要再提供证明了。我只不过想成为这个转轨进程中的一个参与者。这不光是我个人的理解和选择。大多数文学从业者都从九十年代开始转向影视,今天中国的一线作家没有接触过影视的微乎其微,要么是作品被改编,要么是自己参与编剧,深度介入影视创作制作的也大有人在。
独舌:但为什么传统作家转行做编剧成功的例子好像并不多? 梁振华:我个人觉得有几个原因,首先纯文学精英写作是以个人的心性、情怀和对世界的理解为根基的个性表达,自我是最高律令。这种创作是向内走的;但影视创作是向外走的,始终处于被外界审视的过程中,它的对话结构要比纯粹向内走的创作更复杂。你要跟作品的出品方对话,要跟作品的播出方对话,更要跟这个作品的观众对话。这三个对话关系摆在你面前,势必会逆向地对创作构成影响。在自我受到严格规训的情况下,个性美学的写作就变得举步维艰。第二个原因,两种叙事有很大的本体差异。编剧常讲情节、讲故事浓度,因为观众看一部剧,不光是读一个创作者对世界的感悟,他要看到戏,要看到人和事件的戏剧性构造。内心的东西也要藏到叙事性的内容里面去。有些纯文学创作者习惯了诗性的表述,而可能会忽略“戏”的成分。小说可以写得很散淡冲和,故事性并不是小说第一性的要素,小说很大一部分魅力来自语言。但如果换了影视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语言自身的魅力在剧本中是无法自足的。 独舌:但是也有共同的东西吧? 梁振华:当然,共通的就是对人与现实的观照。如果艺术都是基于一种对存在的发现性揭示的话,那么小说叙事和影像叙事都可以做到。只要能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去切入存在(包括人性、现实和历史),这个视角就是艺术性的。艺术相对于现实生活具有某种超越性,这也是两者的区别。 (3)趣味嬗变,取中和之路 独舌:在您写随笔评论的那个时期,也有关注电影和电视剧吗? 梁振华:我大二就当了湖南师大影评协会的会长,经常要在岳麓山下组织学生看电影、写影评,忙得不亦乐乎。我曾经给一部电影写三篇影评,从不同的角度去评论,然后发在不同的报纸上。重要的不是你的结论,而是你的角度。围绕一个作品,可以从无数角度得出观点。当时还办过一个校园杂志叫《电影沙龙》,在一间办公室里憋了三天三夜,写出了我人生中第一部电影剧本叫《碧血英魂》,根据《东周列国志》里的一个典故改编的,可惜这剧本找不到了。后来一直给纪录片做撰稿人,直到2007年写了第一部电视剧《密战》。《密战》讲的是保密,是一部当代谍战戏,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手段,我把一些美剧的叙事元素和中国式伦理进行了“混搭”,这部作品2009年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很高,记得当年全国排名第三。
独舌:这些年来,影视剧主流观众的趣味有什么变化? 梁振华:时代主流的审美趣味在变,而且非常快,这个变快的幅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很多经典现实主义的作品、很正很传统的东西,许多八零后、九零后可能接受不了、喜欢不起来。他们的趣味跟那个文化层面的趣味对接不上。不能说谁错了,只是对接不上。传统型的创作,其意义和价值毋庸置疑的,但为什么收视率就是上不去,因为时代趣味在发生变化,年轻人不愿意听,他们受当下网络文化的影响太深。这是全行业今天碰到的最大现实。这个时候创作者有几种选择:第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继续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讲述;第二种,是无视和漠视,抛去一个冷眼,或者指责时代风潮和大众趣味太低俗;第三种选择则是中和的,说你等会儿,我给你讲个段子先。先想法让你停下脚步,听到讲故事人的声音,然后才有接轨、进而改造他们的可能。 独舌:这两年网剧在年轻人中很热,会考虑尝试吗? 梁振华:想去尝试。新鲜的媒介渠道,要求新鲜的表意方式与其匹配。网剧的大潮很快要来袭了,好像人人都这么说。
独舌:您觉得网剧相对传统电视剧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梁振华:我没有做过网剧,凭我现阶段的理解,觉得有几点:第一,要敢于自嘲和戏谑。第二,带有文化上的某种边缘色彩,跟主流趣味构成差异性。第三,情节浓度、人物的极致程度和事件的特异程度,一定要超过传统电视剧。第四,要有话题性。还有一点就是叙事的拼接色彩和碎片化特征,这也是由互联网的自身文化特征带来的。 独舌:您比较青睐什么题材? 梁振华:这些年,我尝试在不同题材间的创作跨越。《冰与火的青春》是青春励志,《神犬小七》写的是人狗都市情,《怒江之战》《战火红颜》是抗战剧,《密战》当代谍战,《新青年》是年代传奇,《博士老公》则是家庭伦理……我试图从不同的题材里找到能够跟自己创作观念对接的东西,这也是创作的乐趣所在。做编剧的最大乐趣,就因为可以创造无穷无尽的虚拟世界,然后体味不一样的情感和人生。任何一个类型固然都有它的基础规律,但究其根源还是写人,写人与现实的矛盾及其和解。 独舌:今年IP成了行内热词,您会考虑做网络IP开发吗? 梁振华:其实对创作者来说,IP就意味着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在别的媒介上获得了认可,能够预期关注度,就成了IP。它的意义基本上是从商业运营和产业链开发的角度来定义的,跟创作没有关系。当一个IP认可度相当高的时候,当然是一件好事,谁不愿意没拍就有上千万潜在观众;前提是要有作为创作者的能动性,改编和原著应该是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依附的关系。影视剧创作无非两种,一种是原创,一种是改编。IP对创作者来说就是改编一个文本,这并不新鲜。但我觉得很成问题的是,业内很多公司都在孜孜不倦地囤积IP,认为把这块地圈到手就大功告成,后端的转轨毫不在意。只谈IP的占有而不谈IP的开采转化,是难以理解的,很快负面效果就会显现。一个IP在编剧手上变成一个可供拍摄的成熟剧本,最终变成一部剧,这个转轨的过程相当漫长和艰难,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独舌:网络IP改编和以往常规改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梁振华:IP改编,需要适当考虑一下它的核心价值。它之所以成为一个IP,根本原因在哪里,网络上读者到底喜欢它什么。找到这个核心价值,在改编过程中尽量保留它。至于具体的情节设计和细节层面,应该遵循影视的艺术规律,而不是迁就IP本身。如果可以直接拿着书就照着拍,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可以取缔编剧这个行业了。
独舌:您不拒绝IP,可是更喜欢原创? 梁振华:原创永远是最大的生产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原创永远能给人一种陌生的惊喜。创作一个作品,把内容精良程度、独特性、市场匹配度做到最好,自然会成为IP。我坚信。 (4)做制片人是为了主导作品的趣味 独舌:《冰与火的青春》是您第一次做制片人吧,谈谈为什么从编剧转到制片领域? 梁振华:做编剧这些年,写《密战》是两年,《新青年》是三年,《我的博士老公》三年,《冰与火的青春》从剧本创意到播出是四年。编剧的每部作品背后都是血泪史,这一点都不夸张。影视工业有它的流程,编剧这行需要合作,跟诗人、小说家的那种个体化创作不一样,一定是处于各种力量的博弈中,这我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做编剧,得有足够的心胸去面对和处理各方面的意见,什么意见也听不进的人不适合做这一行。问题是,很多时候你拿到的意见真的是拍脑袋式的,或者纯粹出于一些个人趣味,你明明意识到他的意见不是给剧本加分,而是减分,但出于话语权的不对等,又必须听从,那种内心撕裂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作为编剧,丧失了创作的自主性,完全被别人的趣味所左右,那就成了码字工,成了个键盘让别人打。大家当然可以来提意见,但最后应该是编剧择其善而从之,区分意见的优劣,选择性地采纳。而只有成为制片人,才有了这个决定权,趣味的决定权,才能够把自己的趣味变成这部剧的主导趣味,把自己想要表达的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我之所以尝试做制片人,也是想把一部剧从无到有、从创意到播出的整个流程都走一遍,影视创作的所有环节都是息息相关的,深度接触到各个工种和环节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剧本创作,会有更深切的感悟和认识。 独舌:《冰与火的青春》历经四年,作为编剧在前期是不是遭遇到很多磨折? 梁振华:这个本子流转了好多家公司,都说好,可是都不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为什么”,我想我的无数编剧同行都问过,今天编剧的项目存活率能达到30%就非常不错了。不拍的理由可能有很多,导演没找到、演员没找到、资金没有到、还要调剧本、还要改风格……只要一个理由,剧本就可以无限期搁置。后来终于有导演介入了,我很高兴,可每次交流,他都彻底颠覆自己上次的意见,分集大纲和前十集剧本颠覆性地重写了四遍。有一天,他又说要把主人公改成反串艺人,因为看了个电视节目,觉得反串艺人很有意思。跟我合作的编剧崩溃了,说梁老师我不干了。我跟她谈了很久,说如果坚持未必知道结果;但如果放弃肯定没有结果。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从双井坐地铁回通州,哭了整整一路。第二天,我跟版权方说,我要把剧本买回来自己干。那几稿全部废掉,回到原点。现在播出的成片,就是以第一稿剧本为基础的。想起这一段经历,我要感谢自己的坚持。是的,我活生生被逼成了一个制片人。
独舌:本子买回来之后呢? 梁振华:第一次做制片人,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找投资、谈演员导演、组班子……从前年12月份把本子拿回来,到去年6月3号开机,到9月1日杀青,再到后期和发行,其间几次投资方以五花八门的理由撤资,各式各样的波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这里最要感谢的是始终与我风雨与共的团队,谢谢他们和我一起,坚持走过了这一段冰火交织的旅程。 独舌:现在摸清了产业的来龙去脉,再回过头来想,会不会对以前自己当编剧时所受的那些规训有新的理解? 梁振华:有理解的地方,也有不理解的地方。一方面,有了项目运作的思维后,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影视剧项目要受到哪些方面因素的制衡和影响。当然,在项目的所有元素中剧本是最具核心价值的,但如果纯粹站在编剧立场考虑问题,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做了制片人后再回头看,发现原创编剧的许多坚持确实是对的,只有坚决排除那些横生枝杈、似是而非的信息干扰,才能在创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长。 独舌: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梁振华:正在筹备一部大历史剧,《思美人》,写屈原的一生,告诉今天的观众:时代、历史和人性怎样把一位旷世诗人推向了汨罗江。“思美人”是屈原《九章》中的诗篇,此处“美人”有三重意思,一个是“美人”,不仅貌美而且品德高洁;第二个是“美君”,美好的君主,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赏识自己的知音;第三是“美政”,屈原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美好清明的政治理想。这部剧有朝斗宫争,有纵横风云,也有凄美爱情和智慧谋略。屈原作为诗人改革家,会有一些内容与当下现实对话共振。故事里还会出现庄子、孟子、张仪、苏秦、孟尝君、宋玉这些历史名人,甚至会出现屈原诗中的若干想象性人物……那是个思想大解放、个性大舒张的年代,处士横议,所有人都活得特别有姿彩。这会是一部情怀厚重的作品,但我会尝试用轻盈飘逸的方式去书写。作为一名湘人,写屈原是长久以来的夙愿,剧本酝酿了近五年,该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了。 【文/掌花案】 End |